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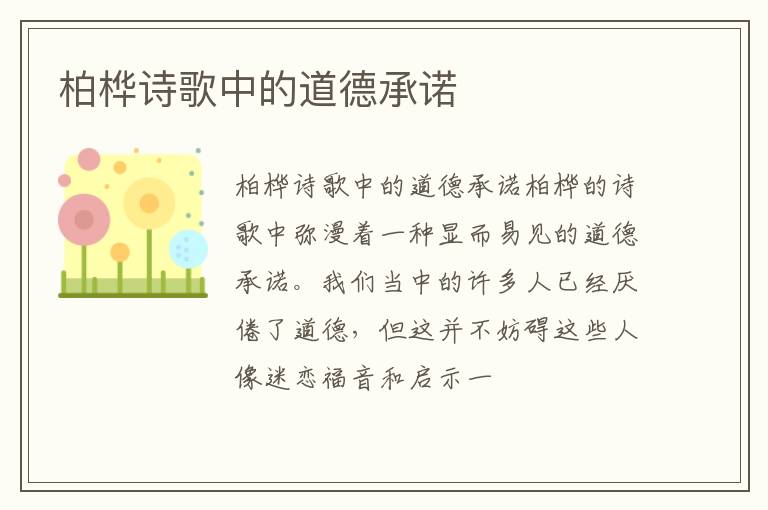
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
柏桦的诗歌中弥漫着一种显而易见的道德承诺。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厌倦了道德,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人像迷恋福音和启示一样地迷恋柏桦式的道德承诺。这似乎是个谜。当然,这不是那种荷尔德林式的发源于清凌凌源头的不可解之谜,柏桦的诗歌并非追根溯源的文化返祖图像;这也不是一种学说、理想或一个时代的终结之谜,更非终结之前的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环节之谜。指明这个谜比解开这个谜更加重要,因为它涉及了隐含于写作深处的道德歧义。很难判定它属于美学的范畴还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是一个形而上的玄想还是一个语义分析的命题。我们的灵魂通过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之谜,无异于文明通过消失点:往后的一切要么是终端,要么还没有开始。在这里,作为谜中之谜,柏桦的道德承诺既非巴尔特式的纯粹形式之确立,亦非萨特式的目的之区分、责任之担负;既不带走可能被肢解的词的空间,也不留下曾在其间停留和经过的技艺上的痕迹。在虚拟式和命令式这一对极关系中,柏桦的道德承诺保持了一种语义上的锋芒和超语速,正是这种速度和锋芒把柏桦的写作引向了可怕的深处,并且把伤害变成了对极乐和忧郁的双重体验。但伤害首先是针对写作者本人的,这直接导致了柏桦诗歌写作的减速。同样的换挡和减速现象也曾在茨威塔耶娃的写作生涯中出现过。所不同的是,茨威塔耶娃的减速是通过从诗歌写作到散文写作这一引人注目的转换完成的,其代价是放弃诗歌写作;而柏桦的减速则是在诗歌写作的特定范围内完成的,减速不过是对他的语言速度的一种限制和缓冲。
如果按照巴尔特对写作的划分,柏桦的写作属不洁之列。巴尔特坚持认为只有一种写作是纯洁的:即零度的、中性的、“不在”的、毫不动心的、拒绝介入的写作,它消除了语言的社会性和个人神话性,并通过信赖一种既远离真实语言、也远离文学语言的“碳性”语言得以从文学本身超脱出来。以这种巴尔特式的写作乌托邦标准来衡量,柏桦的诗歌写作显然是不洁的:他的写作是文学化的,其基本美学特征是倾斜、激动人心、白热化、有着眼点和有趋向性、充斥着个人神话、充满着对美的冒险之渴望、对权力的模棱两可的刺探和影射。换句话说,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是具有某种实质性的,它一点没有因为其诗歌对象的幻象化或行文语气的虚拟性而被稀释掉。这种实质性,有时候体现为对某些残忍的超道德事态(往往是政治化的)做出抒情反应和美学处理的能力,有时候又混合着对权力的奇特渴望及对权力所带来的灾难的近距离审视、作证,还有的时候仅仅是从人生的极端事件向美的组织、美的单元的一种过渡,例如琼斯敦美人。柏桦诗歌中的正义感绝非普遍意义上的正义感。他的道德承诺不仅仅是一种号召和命令,而且是一种分享和告慰,它赋予那些看上去异常简单的事物以回肠荡气的、感人至深的力量。柏桦在写作方式上是不洁的,他所处理的题材和情感(如权力、愤世嫉俗、怀乡病和怀古之思、世纪末情绪)也是不洁的,但柏桦却如得神助般地成了纯洁的象征。这是柏桦的又一个谜。柏桦的正义感、柏桦的道德承诺、柏桦的纯洁是这样一种火焰:熔沧桑之感和初涉人世的天真于一炉;是这样一种黑暗:如果它同时是光的伟大借用者的话,它拥有光的轮廓但其大质量的内涵又显然不是光所能吸取和透过的;是这样一种告慰:它为人的理想所带来的深度忧愁提供了一种可长久珍藏的遗忘的对称形式。置身于这样的道德承诺之中,我想,柏桦本人一定看到了某种悲天悯人、高不可问的天意。
我注意到,道德歧义从写作的深处给柏桦的诗歌带来了出人意料的语言格局。名词由于词性、音位和读速的改变而暗中注入了动词的能量;动词往往无迹可寻或悬而未决,落不到实处,也就是说,与虚词混而不分;而限制词所限制的对象则比未经限制的对象拥有更大的动态范围。这种词法的转换造成了近乎失语症的词的瞬间晕眩,它根源于句法的转换。句法转换的两个特殊形象曾被沃尔夫冈·凯塞尔表述为“脱落”和“省略”。前者涉及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它依赖于相同的句法构成;后者则为转换不偏离要害和终点提供了细节上的保证。对于柏桦来说,转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柏桦的写作中的确存在巴尔特所指出的双层空间和不等时的两种时间制。所谓两种时间制是指历史本身的时间制和史书中的时间制,巴尔特曾举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为例说明两种时间制的差异:同样的文字内容、同样的页数所覆盖的历史时间不可等量齐观,或者二十年,或者几世纪,或者几天。这两种时间制的差异不同于柏格森的主观时间(心理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差异,它像适合于历史写作那样适合于诗歌写作,因为它暗示了诗歌写作中“双关语式”的可能性。“双关语式”源于对索绪尔“换音选词法”的研究,它表明写作是在两个不同层次上进行的。这种写作方式保持着作者的某一具体作品的文本与作者的其他作品的文本之间、与作者的全部作品(包括尚未写出的作品)之间、甚至与整个文学史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双关语式”的写作类似于音乐史上的复调音乐,转换在其中不仅仅是一个词性和词法、句法问题,而且是一个与速度、深度、凝聚力和扩散力有关的语言形象问题。鬼斧神工般的转换意味着柏桦的语言不是线性的,而是不同传递系统、不同语言形象的穿插、交错、替换、吻合。形象对于柏桦而言,是一种权力上的要求,是比寓言更为迫切的道德承诺的具体呈现,是语言的恋父情结,“年轻人由于形象走上斗争”(柏桦美人)。形象属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属于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局面,是承诺和转换、伤害和恢复的奇特产物,但终得以统一。在正常情况下,柏桦的形象转换提供了对写作深处的道德歧义的一种观看和理解;在极端的事态中,他的形象转换则将危险和灾难强加给灵魂,无论我们的灵魂是否准备承受、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些危险和灾难。在两种情况下,柏桦的诗歌都使我们对美的感受和对词的理解发生了倾斜。这使我想起晚年的阿赫玛托娃所津津乐道的布罗茨基献给她的一句诗:你将把我们的事情写成斜行。她认为这句诗注意到了她的书写格局,即每一行诗都向上倾斜,这与她内在的灵视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柏桦式的倾斜则是另一种倾斜,其基本的书写格局是:每一行诗都是平行的,但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有些倾斜。
1990年元月14日于成都
-
天雨萧萧滞茅屋,空山无以慰幽独。锐头将军来何迟,令我心中苦不足。数看黄雾乱玄云,时听严风折乔木。泉源泠泠杂猿狖,泥泞漠漠饥鸿鹄。岁暮穷阴耿未已,人生会面难再得。忆尔腰下铁丝箭,射杀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
-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 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逆其根, 则伐其本, 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 万物之终始也, 死生之本也, 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
名言: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 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逆其根, 则伐其本, 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 万物之终始也, 死生之本也, 逆之则灾害生,
-
戴叔伦 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 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 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 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 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 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
-
题兰溪寺曾栽数十丛,紫茎绿叶领春风。年来萧艾过三尺①,白首看图似梦中。①萧艾,野蒿,臭草。屈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
-
斜凭绣床愁不动,红销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
当代杂文集。吴南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这是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用笔名吴南星合写的杂文结集。收杂文65篇。初载于1961—1964年《前线》杂志。题材亦古亦今,都是作者“随自己的意向
-
许杰 上 吉顺和他的两个朋友匆匆的走上了三层楼,就在向东的窗口择了一个茶座。堂倌来了,问他们要吃什么东西。吉顺吩咐他先泡两壶绿茶,再拿几碟瓜子和花生。 三层楼是我们县里新修的第一间酒菜茶馆,建筑有些仿
-
折桂令·湖上饮别 张可久 傍垂杨画舫徜徉。 一片秋怀。万顷晴光。 细草闲鸥。长云小雁。乱苇寒响。 难兄难弟俱白发相逢异乡。 无风无雨未黄花不似重阳。
-
东家壁土恰涂交 〔2〕 ,西舍厅堂初了 〔3〕 ,南邻屋宇重修造。弄泥浆直到老,数十年用尽勤劳。金张第游麋鹿 〔4〕 ,王谢宅长野蒿 〔5〕 ,都不如手镘坚牢 〔6〕 。 〔1〕双调,曲调名。水仙子,
-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原文、赏析、作者表达什么思想情感?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杜审言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杜审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