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李商隐《花下醉》全诗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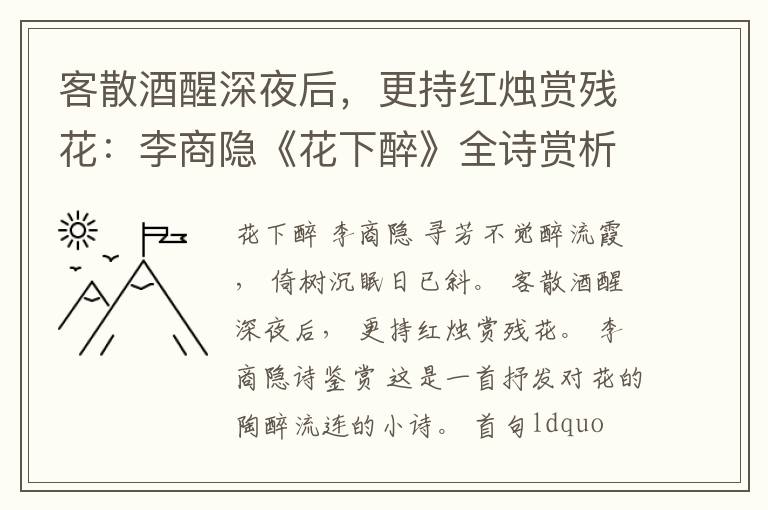
李商隐
寻芳不觉醉流霞,
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
更持红烛赏残花。
李商隐诗鉴赏
这是一首抒发对花的陶醉流连的小诗。
首句“寻芳不觉醉流霞”,写出从“寻”到“醉”
的过程。因为爱花,所以怀着浓厚的兴趣,殷切的心情,特地独自去“寻芳”;既“寻”而果然喜遇;既遇遂深深为花之美艳所吸引,流连称颂,不能自已;流连称颂之馀,竟不知不觉地“醉”了。这是双重的醉。流霞,是神话传说中一种仙酒。论衡上说,项曼卿好道学仙,离家三年而返,自言:“欲饮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每饮一杯,数日不饥。”这里用“醉流霞”,含意双关,既明指为甘美的酒所醉,又暗喻为艳丽的花所醉。从“流霞”这个词语中,可以想象出花的绚烂、美艳,想象出花的芳香和形态,加强了“醉”字的具体可感性。究竟是因为寻芳之前喝了酒此时感到了醉意,还是在寻芳的过程中因为心情飘飘然而对酒赏花?究竟是因迷于花而增添了酒的醉意,还是因醉后的微醺而更感到花的醉人魅力?很难说得清楚。可能诗人正是要借这含意双关的“醉流霞”表达出生理的醉与心理的醉之间相互作用和奇妙融合。“不觉”二字,正传神地描绘出目眩神迷、身心俱醉而不自知其所以然的情态,笔意极为超妙。
次句“倚树沉眠日已斜”进一步写“醉”字。因迷花醉酒而不觉倚树(倚树亦即倚花,花就长在树上,灿若流霞);由倚树而不觉沉眠;由沉眠而不觉日已西斜。叙次井然有序,而又处处紧扣“醉”字。醉眠于花树之下,整个身心都为花的馥郁所包围、所熏染,连梦也带着花的醉人芳香。所以这“沉眠”不妨说正是对花的沉醉。这一句似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迷花倚石忽已暝”句化出,进一步写出了身心俱醉的迷花境界。
醉眠花下而不觉日斜,似已达到迷花极致而难以为继。三、四两句忽又柳暗花明,转出新境--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倚树沉眠中,时间不知不觉由日斜到了深夜,客人已经四处离去,酒也已经醒了,四周是一片夜的朦胧与沉寂。在这种环境气氛中,一般人是不会想到欣赏花的;即使想到,也会因露冷风寒、花事阑珊而感到意致索然。但对一个爱花迷花的诗人来说,这种酒后人醒的深夜气氛,反倒更激起赏花的意趣。酒阑客散,正可静中细赏;酒醒神清,与醉眼朦胧中赏花自别有一番风味;深夜之后,才能看到人所未见的情态。特别是当他想到白天盛开的花朵,到了明朝也许就将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深刻留连之情便油然而生,促使他抓住这最后的时机欣赏行将消逝的美,于是,便有了“更持红烛赏残花”这一幕。在夜色朦胧中,在红烛的照映下,这行将凋零的残花在生命的最后瞬间仿佛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华,美丽得像一个五彩缤纷而又隐约朦胧的梦境。诗人也就在持烛赏残花的过程中得到了新的也是最后的陶醉。夜深酒醒后的“赏”,正是“醉”的更进一步的表现,正如姚培谦所说,“方是爱花极致”(李义山诗笺注)。清人马位说:“李义山诗‘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有雅人深致;苏子瞻’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有富贵气象。二子爱花兴复不浅”(秋窗随笔)。“雅人深致”与“富贵气象”之评,今天我们也许有所保留,而归结到“爱花兴复不浅”,则是完全确切的。
-
苏子由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
-
冬宵寒且永。夜漏宫中发。草白霭繁霜。木衰澄清月。丽服映颓颜。朱灯照华发。汉家方尚少。顾影惭朝谒。
-
项脊轩 ① ,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 渗漉 ② ,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 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
-
《林下风致》出处、释义和例句 【出典】《世说新语·贤媛》:“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杜审言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首二句言
-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後。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 作品赏析题又作:新晴晚望这是一首田园诗。描写初夏的乡村,雨后新晴,诗人眺望原野所见到的景色。诗的开
-
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已过爱贪声利后,犹在病羸昏耄前。未无筋力寻山水,尚有心情听管弦。闲开新酒尝数盏,醉忆旧诗吟一篇。敦诗梦得且相劝,不用嫌他耳顺年。
-
洛阳女儿行 王维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①容颜十五余。 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 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 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②。 狂
-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
形诸文字的泰国近代文学批评如果从天宛评论顺吞蒲的长诗《帕阿派玛尼》的时间算起,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有趣的是天宛的开篇文章还是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