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词精品之《一、不知其人可乎》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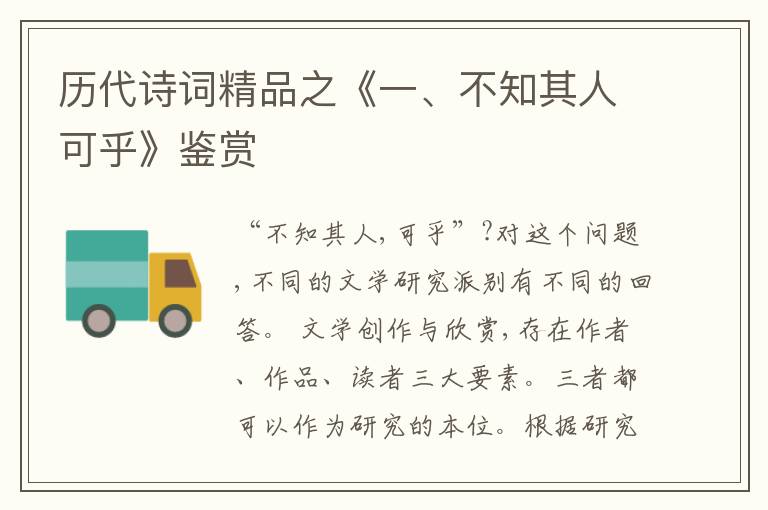
文学创作与欣赏,存在作者、作品、读者三大要素。三者都可以作为研究的本位。根据研究对象择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和方法。持作家本位的实证主义批评,将文学研究等同于考据,着重对作品产生的背景的探究;持作品本位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则着重对作品的语言结构的探究;而持读者本位的接受美学理论,强调作品的未定性,更多着重于作品的功能的研究。各种方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有理有效。但如果各执一偏,相互排斥,那显然与系统论的方法相违背。在“知人”这个问题上,尽管不同的文学研究派别看法不一样,但在实际欣赏活动中,“知人”构成一种欣赏的前提条件,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文学作品情况千差万别,很难执一而论。“知人”的必要程度,也应视具体对象而定。
“诗言志”(尚书·尧典),“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很早人们就认识到诗歌这种体裁,是以表现或抒情为特征的。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多为诗人自我形象,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带有诗人的影子。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我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一向重视“知人”,西方的文艺批评几乎也不谋而合。如近代法国文论家申徒白吾便以为研究作品应当先从作者的人格、状态、遗传、境遇、生涯诸方面着手,通过这“媒层”,方可洞悉作品的意蕴。唯西方现代新批评派反对这种方法,认为作者生平事迹除了帮助我们了解某些用词含义和私人生活的影射,没更多的用处。比如大谈济慈如何在花园里听到夜莺的歌声,与我们评价夜莺颂这首诗实在无甚相干。(参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种反对意见虽然确实刺中了某些考据成癖或为考据而考据的文艺批评的痛处,却有较大片面性。因为即便都是诗歌,其表现形态也有千差万别,不可执一而论。就某些抒发常人较普遍情感的诗作如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具有较明显的象征意义的诗作如王之涣(实应作朱斌)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了解作者生平的确无妨于欣赏。然而更多的情况则是诗人的创作具有某种特定环境、特定的人事关系,抒发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诗作具有艺术个性。因此,如果读者对作家生平一无所知,对于创作的背景一无所知,那么他对于这一作为个体创作的精神产品,很可能是一知半解,甚至于产生误会。倘使他仍对此津津乐道,便成一则笑话所说的瞎子品味鱼汤,而不知鱼尚未丢进锅内。青年朋友未具“知人”之明而误会古代诗词的例子所在皆有,似不必小题大作,多加揶揄。然而名家忽略了知人说诗,闹出笑话来,那影响就不一样了。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交谊甚厚,颇有诗歌往还,这在今天稍有文学史知识的读者也有所了解。因为杜年辈晚于李,故杜赠李之诗作尤多,如以下二诗: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君)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
倘若今日有人说这二诗是以“前辈”身份教导“后学”,岂不令人哑然失笑?殊不知犯这个卤莽灭裂的大错误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评解“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的金圣叹,在他的名著杜诗解中对前二诗解道:
眠何必共被?行何必携手?此殆言己(杜甫)无日无夜不教侯(李白)作诗。读他日“重与细论”之句,盖先生之教之,不信然哉!
读“飞扬跋扈”之句,辜负“入门高兴”、“侍立小童”二语不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见前辈交道如此之厚也。
本来金圣叹的诗文评,是以纵横老辣,明快如火,常发人所未发见称的。但这位评“才子书”的才子,才子气实在太重。他既不重杜诗之编年,也不重写作的历史背景,堂堂杜诗专家而不知李杜年辈之少长,也实在太令人费解了。(估计这一误会,是由误解杜甫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二句而来的,盖古人称呼“生”乃“先生”的意思,与后来称呼年轻人为“生”,不能混为一谈。)如此忽略知人论世,而一味主观意逆,忽略考据而欲阐发义理之精微,也就难免说错话。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答曰:不可也。
-
本文主要为您介绍山和云的古诗词,内容包括描写“山和云”的诗句,山水云的诗句大全,描写山,水,云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 白帝城》2、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
皮日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今人称为大运河,即隋炀帝时疏浚开掘的通济渠,因其主干在汴水一段,故唐以来,人们习惯上呼为汴河。隋大业元年,炀帝发民工百
-
南朝乐府民歌始欲识郎时, 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 何悟不成匹!这首民歌,是写一个
-
作者: 张翼之 《二十二史札记》三十六卷,清代赵翼撰
-
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幔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
-
在李商隐诗中,具体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观赏、对山村野趣的忘我流连。诗歌首联写与田叟相逢之情景。颔联写所见所闻,皆为田园生活之景。颈联把田叟不以世事为怀与官场得志升官者进行对比,一歌颂一讽刺,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尾联用野无遗贤典故,既赞美
-
读书头欲白,相对眼终青。身更万事已头白,相对百年终眼青。看镜白头知我老,平生青眼为君明。故人相见尚青眼,新贵如今多白头。江山万里将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
-
【原题】:登普宁寺岁寒庵面江山之胜令人欲赋而长老因公出诗集相示作此诗谢之
-
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况当营都邑,杞梓用不疑。张侯嵩高来,面有熊豹姿。开口论利害,剑锋白差差。恨无一尺捶,为国苔羌夷。诣阙三上书,臣非黄冠师。臣有胆与气,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语,不能伴儿嬉。乃著道士
-
高门元世旧,客路晚追游。清绝闻诗语,疏通岂法流。传家有衣钵,断狱尽春秋。邂逅陪车马,寻芳谢朓洲。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恨赋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字律,相与一樽留。更约登尘外,归时月满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