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悼亡诗(其一)》赏析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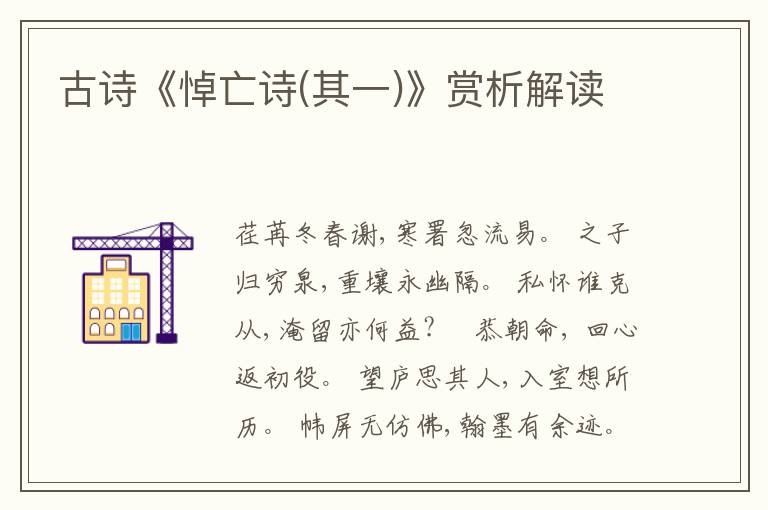
荏苒冬春谢,寒署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俛恭朝命, 回心返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怳如或存,周惶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中年丧偶,乃人生的一大痛苦和不幸。对于多愁善感而又多身世坎坷的中国古代文人,这种痛苦显得尤为刻骨铭心。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就产生了一种悼亡文学,而这种悼亡文学的开山之作,则可说是晋代作家潘岳的 悼亡诗 。
潘岳所生逢的魏晋时代战乱频仍、动荡不已,赳赳武夫叱咤风云纵横天下,而文人的日子普遍不太好过。因此,尽管潘岳“才名冠世”,姿仪美艳,然而却不得不违心地依附于权门贵胄、军营幕府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对于这样一位才貌绝伦、自视甚高而又遭遇坎坷、无人赏识的人来说,内心的孤独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能有一个温柔、贤淑的妻子,一个温馨、宁静的家庭,该能给他受伤的心多少温暖、多少抚慰?然而不幸的是,死神偏偏与他作对,先后夺走了他的弟弟、妹妹、儿子,最后又残酷地夺走了他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的爱妻,这怎能不叫他肝肠寸断呢! 而悼亡诗 正是诗人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之结晶。
现在,我们就看看其三首悼亡诗中的第一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
先看第一层的八句: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荏苒”者,展转之间也,形容速度较快。“谢”,代谢,相互交替。“忽”,快速。“流易”,消逝、更换。二句是说光阴飞逝,时节变易,不知不觉中已是冬去春来、还寒乍暖的早春时节了。也许有人会奇怪,以潘岳这样一位多愁善感的情绪型诗人,怎么会对“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种节候逐渐变化的过程丝毫没有感觉以致发出“寒暑忽流易”之叹呢?须知这首诗作于爱妻甫葬那段极度哀伤、绝望的日子,正是这极度的哀伤和绝望削弱了诗人本来对于节候变换的敏锐感觉,使他变得痴呆人一般,不觉冬春之代谢,寒暑之流易了。这种从流逝的时光入手的开篇方式为后代许多作家所接受,比如现代作家朱自清先生有一篇给亡妇,其开篇那几句——“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即明显地受了潘岳的影响。
首二句着眼于时间,而三四句则着眼于空间。“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之子”,犹伊人、那人,代亡妻。“穷泉”,犹今所谓“九泉”。“重壤”,层层土壤。“幽”,深邃。“幽隔”,谓被阻隔在深邃的地下。二句是说妻子已亡归地下,永远被土层隔绝了。在首二句中,诗人则从丧偶的哀伤中抬起头,惊觉时光之流逝,而在三四两句中又重新陷入阴阳难合、幽明难通的哀叹,足见诗人怎么也无法走出失去爱妻的阴影。
是的,对于任何深于情,痴于情的人来说,要即刻走出这种丧偶的阴影谈何容易?然而在潜意识中,又不是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甘愿走出这片阴影,走出这片曾经是那样熟悉,温馨的生活天地的。此时的潘岳正是如此。尽管家中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只能勾起他伤心的回忆,然而诗人还是愿意滞留家中,在痛苦的回忆中追寻亡妻的音容笑貌、丰姿仪态。然而为了某种不便言说的原因,他必须强忍痛苦,离家赴任,此即诗人所谓“私怀谁克从”。“私怀”,私愿。指 “哀伤私情,欲不从仕” (见 文选吕延济评语)。“克”,能够。“从”,随,顺从。既然本意 “欲不从仕”。可见下句的 “淹留亦何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一种自嘲。不是滞留在家里没什么益处,而是迫不得已,不得不从仕。
关于这一点, 从下面紧接着的两句 “��俛恭朝命, 回心返初役”可以看得更清楚。 “��俛”, 勉强、 迫不得已。 “恭朝命”, 顺从朝廷的任命。 可见“恭朝命”而赴任是迫不得已之事。“回心”,即转换念头,扭转心情。“初役”,原任官所。二句是说只好顺从朝廷的任命,扭转心情回原任官所去。
以上八句是全诗第一层。写服丧期满,不得不离家赴任。如果将这首诗比作诗人献给亡妻的一首哀歌的话,那么,第一层可以说是一个慢板引子,只是把读者逐渐引入诗人所营造的环境气氛中,直到下面的第二乐章才展开了 ‘淋漓倾注,宛转侧折” (陈祚明评语,见 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的倾吐和宣泄。下面,我们就看看诗人是怎样一吐为快的: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庐”,住宅。“室”,内屋。“历”经过,指妻过去的生活。二句互文见义,即 “望庐”时既 “思其人”又“想所历”,“入室”时既 “想所历”又“思其人”,不可呆看。这两句还只是总领,其作用在于引导出下面六句更为具体的睹物思人、触景伤情的描写: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帏”,帐子。“屏”,屏风。“仿佛”,相似的形影。“翰”,毛笔。“翰墨”,即笔墨。此处指用笔墨书写的文字。“余迹”,犹 “遗迹”。二句一言人影难觅,一言遗物尚存; 一言 “无”,一言 “有”; 貌似相反相对,实则一意贯通。因为不管是 “帏屏无仿佛”,还是翰墨有余迹”,都只能引起诗人满目萧然、物是人非之感。作者在这里几乎是不露痕迹地化用了一个典故: “李夫人早卒,方士齐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帏帐,令帝居他帐中,遥望见少女如李夫人之状,不得就视。”(见 汉书·外戚传)汉武帝的思念已经够难熬的了,然聊可安慰的是尚可在灯烛下依稀遥望到李夫人的仿佛之影,而潘岳却连 “仿佛”之影都无法看到,只能看到亡妻遗留下来的笔墨文字,可见其情思之酸苦绝望更胜汉武一筹。
这种物是人非的境况,煎熬得诗人心神恍惚,几疑自己的神智是否清醒:“怅怳如或存,周惶忡惊惕”。“怅怳”,神志恍惚。“周惶”,很惶恐。“忡”,忧。“惕”,惧。清人吴淇对这二句的评语颇为中肯: “……总以描写室中人所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 (见 六朝选诗·定论 ) 。
以上八句为全诗第二层,总写诗人 “将出未出,流连虚室,触目伤心景象”(清人张玉谷语,见 古诗赏析)。
下面再看第三层。
“如彼翰林鸟, 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 比目中路析” 。 “翰” : 羽翮。“翰林鸟”,指振羽飞翔于林中的鸟。“比目”,鱼名。尔雅·释地: “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析”,分开。四句以双栖鸟成单、比目鱼分离来比拟丧偶后的孤独忧伤之情。
再看最后一层,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隙”,此处指门窗的缝隙。“霤”,屋檐上流下来的水。“寝息”,安寝休息。“庶几”,强作希望之词,犹“但愿”。“庄” ,代指庄周。“缶”,瓦盆。史称庄子死了妻子后,曾鼓盆而歌。缘隙的春风,承檐的晨霤,都在无声地宣告时光的流逝,然而这流逝的春光却带不走郁积于诗人心头的、越来越沉重的忧伤。在百般无奈中,他想起了古代那位“齐万物、等生死”的庄子,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从感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轻松、洒脱地活下去。然而对他这样的“痴人”来说,“鼓盆而歌”谈何容易? “庶几”二字即透露了一切。
最后再补充一点,我们说潘岳的悼亡诗是中国悼亡文学的开山之作,并不是说在他以前绝对没有这类作品,只是在他之前数量极少,而且其形式和表现方法也极其古朴简单。直到潘岳才第一次将“悼亡”二字作为篇名,并且在艺术表现上纵横铺排,反复陈说,惨淡经营出一片浓郁的悲剧气氛,而且后代的悼亡之作差不多都承袭了他所开创的那种与作思路。
-
昔听东武吟,壮年心已悲。如何今濩落,闻君辛苦辞。言有穷巷士,弱龄颇尚奇。读得玄女符,生当事边时。借名游侠窟,结客幽并儿。往来长楸间,能带双鞬驰。崩腾天宝末,尘暗燕南垂。爟火入咸阳,诏征神武师。是时占军
-
旧体诗、词大体上有齐言与长短句之别。但词中也有少数齐言者,这首词基本上一句一意,句子间不免省略叙写与过渡的词语,出现若干空白。这就需要比勘揣摹,发挥联想,方能对词意有充分的体味。 此词的题材是最常见的暮春思妇之闺怨。但用《三字令》这
-
爽砧应秋律,繁杵含凄风。一一远相续,家家音不同。户庭凝露清,伴侣明月中。长裾委襞积,轻珮垂璁珑。汗余衫更馥,钿移麝半空。报寒惊边雁,促思闻候虫。天狼正芒角,虎落定相攻。盈箧寄何处,征人如转蓬。
-
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
-
此词描写离别之情,上半阕发端句写向两边看望,“芳草长川”的横幅画面,即刻收入视野,这幅画里面,既有“同冈揭崔嵬,双阜夹长川”的高山峡谷,也有“芳草萋萋”的水中绿洲。紧接“柳映危桥桥下路”一句,写向前后观看,那高桥如长虹卧空,飞架长川两岸
-
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
-
沈夫子,胡为醉翁吟,醉翁岂能知尔琴。滁山高绝滁水深,空岩悲风夜吹林。山溜白玉悬青岑,一泻万仞源莫寻。醉翁每来喜登临,醉倒石上遗其簪,云荒石老岁月侵。子有三尺徽黄金,写我幽思穷崎嶔。自言爱此万仞水,谓是
-
居藩久不乐,遇子聊一欣。英声颇籍甚,交辟乃时珍。绣衣过旧里,骢马辉四邻。敬恭尊郡守,笺简具州民。谬忝诚所愧,思怀方见申。置榻宿清夜,加笾宴良辰。遵途还盛府,行舫绕长津。自有贤方伯,得此文翰宾。
-
是故智者 ① 之虑,必杂 ② 于利害。杂于利而务 ③ 可信 ④ 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第八》) 【注释】 ①智者:明智的将领。②杂:此指兼顾。③
-
1伏生挑着一担柴,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时候,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各种花都开了,鸟儿们欢快地鸣叫着,空气中弥漫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