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题峡山寺》原文,注释,译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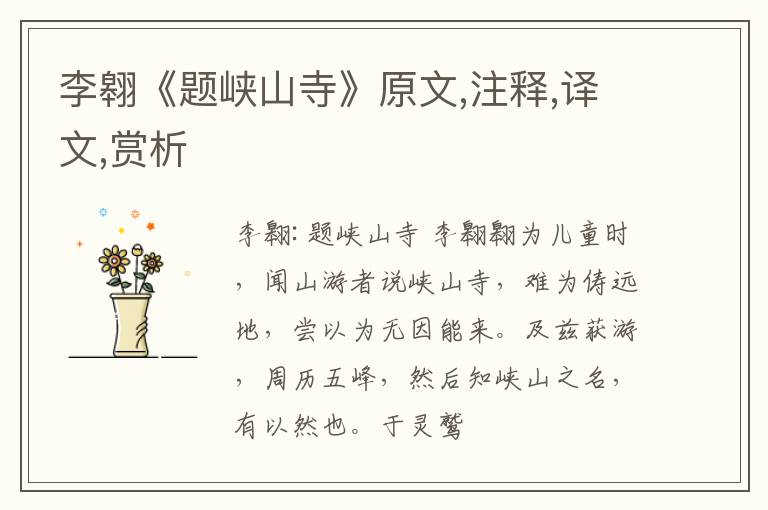
李翱:题峡山寺
李翱
翱为儿童时,闻山游者说峡山寺,难为俦远地,尝以为无因能来。及兹获游,周历五峰,然后知峡山之名,有以然也。
于灵鹫寺时,述诸山居之所长,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剑池不流;天竺之石桥下无泉;台山之力,不副天奇,灵鹫拥前山,不可远视。峡山亦少平地,泉出山,无所潭。
乃知物之全能,难也。况交友择人,而欲责全耶!去其所阙,用其所长,则大小之材无遗,致天下于治平也,弗难矣。
元和四年,李翱应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杨于陵征聘,从长安由广济渠入黄河,转汴河,经淮河、长江、富春江、鄱阳湖、漳江、浈江至广州。在赴职途中,六月初五宿峡山,写下这篇题记。峡山,在今广东清远县南,又名观亭山、观峡、中宿峡。
从开篇至“有以然也”为第一段。追述作者早已听说峡山这一名胜,但因相去遥远,故难以结伴远游此地。幸有这次征聘之行,在遍游许多江南名山之后,得以目睹峡山风采,始信传闻不虚。说明从闻名到目睹的经过。“周历五峰”(虎丘、天竺、台山、灵鹫、峡山)句则为下段对诸名山优劣的评论作揭示。
从“于灵鹫寺时”至“无所潭”为第二段。历数诸名山“所不足”:苏州虎丘山上的剑池是一潭死水;杭州天竺山的灵隐石桥则无涓涓流泉;台山(大庚岭)太险峻,亦无与之相匹配的天然奇观;广东曲江的灵鹫山则前耸高峰,使游人视野无法开阔;而峡山则极峻峭,无一席平地,泉水也只是单调的狭窄湍流,而无潭水点缀其间。作者用诸名山之所短来纠正他在题灵鹫寺一篇中,只“述诸山居之所长”的偏颇。这段对山水的评论,引出了下面物固难全的议论。
从“乃知物之全能”至篇末为第三段。作者从诸名山均各有“所不足”出发,得出“物之全能,难也”的结论。又从这一对万事万物的高度概括,说到交友用人,不应求全责备,而应“去其所阙,用其所长”。如果真能做到这点,作者认为,即使治理好国家这样的复杂事务,也“弗难矣!”从而把议论推向更加深化阶段。
这是一篇山水评议文章,不同于一般的写景的游记作品。作者遍游江南名山之后,在这篇题记中,用简洁扼要的文笔,恰当中肯地评述诸山之不足,很有见地。并从山水之难全,引出议论;从“交友择人”,进而深入到治理国家的道理。引伸转圜,契合天然,毫无榫隙。全文仅一百五十余字,但有叙述,有评说,有议论。文章层次清晰,结构紧凑,文字质朴,主题集中。无论就鉴赏山水,还是治理人事,都能给人以教益和启发。
-
本文将对《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和《邯郸冬至夜思家》进行对比赏析。两首诗都是怀念故乡的作品,但表现手法和情感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前者通过描绘光景和回忆,向读者展示了作者对山东兄弟的思念之情;而后者则以空灵的笔墨,通过描写邯郸的冬至夜景,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两首诗都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让读者对故乡产生共鸣。
-
国学名句“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出处和解释
【名句】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 语出汉代徐干《中论·治学》。君子心中从来不随便产生什么别的念头,有念头那就一定是学习;其身体从来不随便行动,要行动那就一定是去拜师求教。说明君子心无
-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智生, 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 生于匮不足; 匮不足之所生, 生于侈; 侈之所生, 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为国之急也; 不通
名言: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智生, 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 生于匮不足; 匮不足之所生, 生于侈; 侈之所生, 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为国之急也
-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饮咸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于土。预忧一旦开两翅,口吻如风那肯吐。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去岁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极可畏。)农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区区固难御。扑缘
-
《断章卞之琳》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十月三日 《断章》写于1935年10月。据作者自云,这四行诗原在一首长诗中,但全诗仅
-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1250?-1324?),字千里,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他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以后,做过江浙行省务官
-
林景熙《京口月夕书怀》 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 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 ② 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 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 ③ 【注释】 ①京口:今江苏镇江。②华发:花白的头发。百年:此指一生
-
白发逢秋王,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
谒金门 【宋】韦庄 春雨足, 染就一溪新绿。 柳外飞来双羽玉, 弄晴相对裕 楼外翠帘高轴, 倚遍阑干几曲。 云淡水平烟树簇, 寸心千里目
-
张爱玲《谈音乐》赏析 张爱玲这个名字,青年读者或许是陌生的。这也难怪,建国以后出版的文学史,对这位女作家只字不提,致使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与此相反,海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