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的幽灵 台静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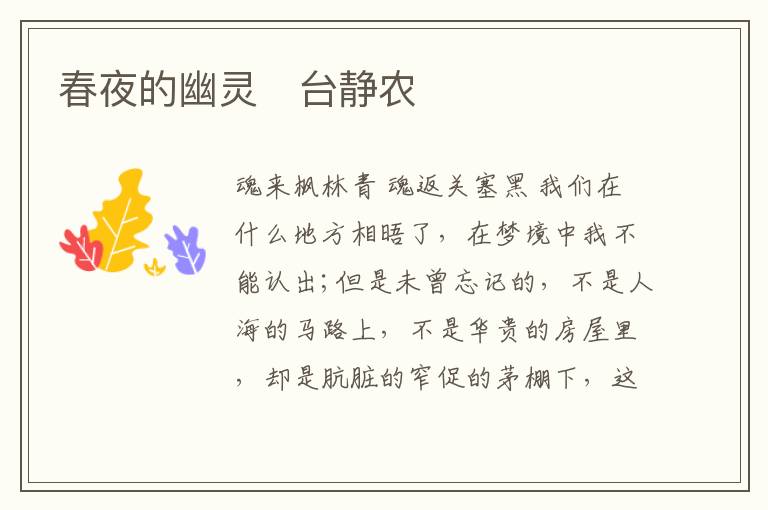
魂来枫林青
魂返关塞黑
我们在什么地方相晤了,在梦境中我不能认出;但是未曾忘记的,不是人海的马路上,不是华贵的房屋里,却是肮脏的窄促的茅棚下,这茅棚已经是破裂的倾斜了。这时候,你仍旧是披着短发,仍旧是同平常一样的乐观的微笑。同时表示着,“我并没有死!”我呢,是感觉了一种意外的欢欣,这欢欣是多年所未有的;因为在我的心中,仅仅剩有的是一次惨痛的回忆,这回忆便是你的毁灭!
在你的毁灭两周以前,我们知道时代变得更恐怖了。他们将这大的城中,布满了铁骑和鹰犬;他们预备了残暴的刑具和杀人机。在二十四小时的白昼和昏夜里,时时有人在残暴的刑具下忍受着痛苦,时时有人在杀人机下交给了毁灭。少男少女渐渐地绝迹了,这大的城中也充满了鲜血,幽灵。他们将这时期划成了一个血的时代,这时代将给后来的少男少女以永久的追思与努力!
“俞也许会离开这个时期的!”我有时这样地想。在我的心中,总是设想着你能够从鹰犬的手中避开了他们的杀人机;其实,这是侥幸,这是懦怯,你是将你的生命和肉体,整个地献给人间了!就是在毁灭的一秒钟内,还不能算完成了你,因为那时候你的心正在跳动,你的血还在疯狂地奔流!
在你毁灭了以后的几日,从一个新闻记者口中辗转传到了我,那时并不知道你便是在这一次里完结了;因为这辗转传出的仅是一个简单的消息。但这简单的消息,是伟大的、悲壮的。据说那是在一个北风怒啸的夜里,从坚冰冻结的马路上,将你们拖送到某处的大牧场里。杀人机冷然放在一旁,他们于是将你们一个个交给了。然而你们慷慨地高歌欢呼,直到你们最后的一人,这声音才孤独地消逝了!自我知道这消息以后,我时常在清夜不能成寐的时候,凄然地描画着,荒寒的夜里,无边的牧场上,一些好男儿的身躯,伟健地卧在冻结的血泊上。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其间。
一天清晨,我同秋谈到这种消息,他说也有所闻,不过地址不在某处的牧场,其余的情形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也不知道其间有你。忽然接到外面送来的某报,打开看时,上面森然列着被难者的名字,我们立刻变了颜色。这新闻是追报两周以前的事,于是证实了我们的消息,并且使我们知道被难的日子,——这一天的夜里,也许我还在荧灯前无聊的苦思,也许早已入梦了,反正是漠然地无所预感。然而我所忘不了的仍是两周后的一个清晨。
报上所登的名字有你的好友甫。回忆那三年前的春夜,你大醉了,曾将甫拟作你的爱人,你握着他,眼泪滴湿他的衣;虽然这尚不免少年的狂放,但是那真纯的热烈的友情,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你们一起将你们自己献给了人间,你们又一起将你们的血奠了人类的塔的基础。啊,你们永远同在!
三年前,我同漱住在一块,你是天天到我们那里去的。我们将爱情和时事作我们谈笑的材料,随时表现着我们少年的豪放。有时我同漱故意虚造些爱情的事体来揶揄你,你每次总是摇动着短发微微地笑了。这时候我们的生活,表面虽近于一千六百年前魏晋人的麈尾清谈,其实我是疏慵,漱是悲观,而你却将跨进新的道路了。
第二年你切实地走进了人间以后,我们谈笑的机会于是少了。但是一周内和两周内还得见一次面的。渐渐一日或两日之久,都不大能够见面了。即或见了面,仅觉得我们生活的情趣不一致,并不觉着疏阔,因为我是依然迷恋在旧的情绪中,你已在新的途中奔驰了。
去年的初春,好像是今年现在的时候,秋约我访你,但是知道你不会安居在你的住处;打了两天的电话,终于约定了一个黄昏的时分,我们到你那里去。你留我们晚餐。我们谈着笑着,虽然是同从前一样的欢乐,而你的神情却比从前沉默得多了。有时你翻着你的记事簿,有时你无意的嘴中计算着你的时间,有时你痴神的深思。这时候给我的印象,直到现在还没有隐没,这印象是两个时代的不同的情调,你是这样的忙碌,我们却是如此的闲暇,当时我便感觉着惭愧和渺小了。
以后,我们在电车旁遇过,在大学的槐荫下遇过,仅仅简单地说了一两句话,握一握手,便点着头离开了。一次我同秋往某君家去,中途遇着你,我们一同欢呼着这样意外的邂逅。于是你买了一些苹果,一同回到我的寓处。但不久你便走了。秋曾听人说,你是惊人的努力,就是安然吃饭的机会,也是不常有,身上往往是怀着烧饼的。
不幸这一次我送你出门,便成了我们的永诀!这在我也不觉着怎样的悲伤,因为在生的途上,终于免不了最后的永诀;永诀于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的心比较得轻松。至于你,更无所谓了,因为你已不能为你自己所有,你的心,你的情绪早已扩大到人群中了。况且在那样的时代中,时时刻刻都能够将你毁灭的;即使在我们热烈地谈笑中,又何尝不能使我们马上永诀呢?
春天回来了,人间少了你!而你的幽灵却在这凄凉的春夜里,重新来到我的梦中了。我没有等到你的谈话便醒了,仅仅在你的微笑中感觉着你的表示“我并没有死”。
我确实相信,你是没有死去;你的精神是永远在人间的!现在,我不愿将你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大地上的人群,将永远系念着你了!
1928年,台静农二十五岁,年轻、热烈的岁月,加之中国纷乱错综的局势。这样的年龄,这样的时代,足以使一个人激烈,狂热,甚至歇斯底里。然而台静农没有,是的,他也哀伤,也彷徨,但是更多的是他那种传统教育之下的传统的宣泄模式,春夜的幽灵就是这种宣泄模式的体现,不是鲁迅的辛辣,不是周作人的恬淡,这篇文章使用一种清澈的呼喊震慑人心,这是对生命的无可奈何的逝去的呼喊,是对社会如此黑暗的呼喊,更是对友人的壮烈事迹的赞美的呼喊。在这里,我们听到台静农年轻的声音,在那个时代中,微弱而不屈地响起。
全文以杜甫诗句开篇,魂来魂返,用“魂”字扣题,带着几分作者的期盼——重逢的梦境,使作者忆起逝去的故人:“我们在什么地方相晤了,在梦境中我不能认出……你仍旧是披着短发,仍旧是同平常一样的乐观的微笑。同时表示着,‘我并没有死!’”
死亡,是最大的哀痛,而在台静农的笔下,不是仅止于哀痛,他所写的是一个时代的恐怖,这种恐怖由大背景给人带来震撼,又由个人的死亡促进了这个大背景的恐怖氛围,台静农的写作顺序就是由此而来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台静农将个人的恐怖升华为一种集体的反思:“他们将这时期划成了一个血的时代,这时代将给后来的少男少女以永久的追思与努力!”于是悼文不再以小儿女的姿态展现,取而代之的是对时代的不认同与对个人精神的赞扬——整篇文章的境界由此而提升。
哀痛也是由惨烈的意象的整合所阐发的:“荒寒的夜里,无边的牧场上,一些好男儿的身躯,伟健地卧在冻结的血泊上。”台静农的文笔虽然是一贯的通明清澈,但是这里,他的对亡友的哀思之情,使他使用了在他的文章中很少再出现近乎壮烈的形容词,也使这篇文章与其后期的隽永风格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困兽的呼号!
当然,台静农的情绪随着行文的渐进而逐渐平静,呼喊转为回忆,在相处中的点滴往事,都因为这回忆的主角的逝去而变得格外的清晰,革命的友谊与爱情,清谈背后的激情,忙碌急迫的身影,随着一个又一个的细节,作者将之不断展示于人。台静农与文中的“你”虽然同为五四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却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所以他的回忆又带着一种“游离的观察”,台静农是擅长这样的描写的,淡然而深远,使人在不经意中被深深感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结尾,在于“我并没有死!”这一句与开篇相呼应,不过,开篇是台静农对故人的眷恋与盼望的虚幻梦境,而结尾则是他对故人精神的肯定与发扬:“我确实相信,你是没有死去;你的精神是永远在人间的!现在,我不愿将你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大地上的人群,将永远系念着你了!”从梦境到走出梦境,这才是文章的独特之处。
在通篇的结构和手法上,作者自由地往返于梦境与现实之间,打破了时空限制,又以“你”“我”的对比贯穿始终,以“我”的疏懒出世反衬“你”的积极入世,使得人物的形象因此而更加丰满。
-
本文主要为您介绍陆游和杜甫的重点文学常识,内容包括陆游和杜甫的资料呀!!,杜甫的文学常识是什么?,杜甫的文学常识。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爱国诗人。父亲陆宰是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教育,
-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全诗,翻译,意思,上一句和下一句
【诗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出处】唐白居易《 长恨歌 》 【翻译】桃花开暖风吹拂的春日过去了,又迎来了雨打秋梧黄叶纷飞的时节。 【解析】不论是春风荡漾,桃李花开的日子,还是秋雨绵绵,梧
-
【注释】:这首悼亡词,写得深曲婉转,语淡而情深,是见作者之词品颇高。开头“晚凉可爱”一句领起了上片词意。经过炎热的夏天,到了初秋夜晚,有些凉意,颇为喜人“是黄昏人静,风生蘋叶 。”在夜深人静之际,习习的凉风吹来,使人郁闷之感全消,就是这个可
-
效西昆体 作者: 金圣叹
-
场藿已成岁,园葵亦向阳。兰时独不偶,露节渐无芳。旨异菁为蓄,甘非蔗有浆。人多利一饱,谁复惜馨香。幸得不锄去,孤苗守旧根。无心羡旨蓄,岂欲近名园。遇赏宁充佩,为生莫碍门。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
-
作者: 崔雄权 【作家简介】河瑾灿,1931年出生于朝
-
【原文】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暮年眼力嗟犹在,多病颠毛却未华。 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 他时夜雨困移床,坐厌愁声点客肠。 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
-
春天的来临,给大观园带来了生机,也给宝玉和大观园女儿带来了萌动的春情,惹起了他们一腔的怀春情愫。 宝玉首先感受到这种春情的萌动,他“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
-
《高阳台》一调,音节整齐谐悦。此词开头“频听银签,重燃绛蜡”就是四字对句的定式。古代计时的器具,每过一刻时光,则有银签铿然自落。“频听银签”,一“频”字,可见守岁已久,听那银签自落声已经多次,说明夜已深矣。“重燃绛蜡”一句,说那除夜灯火
-
原始章·第一 【题解】 注曰:“道不可以无始。” 王氏曰:“原者,根。原始者,初始。章者,篇章。此章之内,先说道、德、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