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铭》原文、赏析和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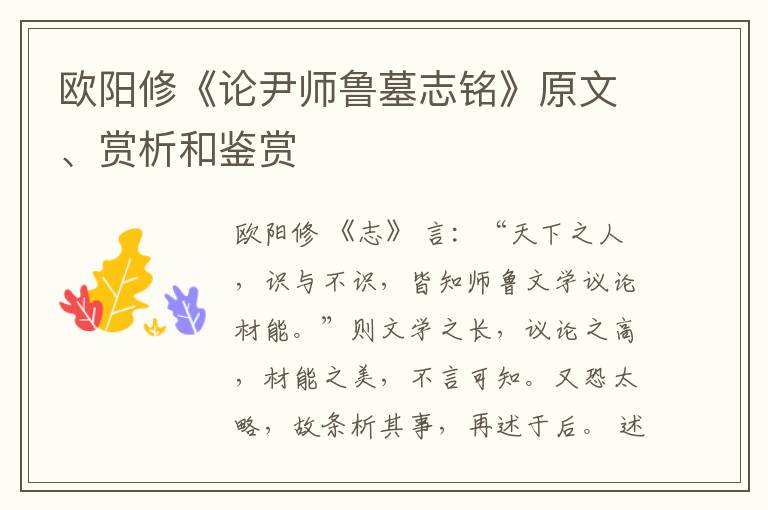
志 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认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只著一句道了。
即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
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
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才能,备言:“师鲁历贬,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才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偏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学、其论议、其材能,其忠义,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一作怨)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
志云: 师鲁“喜论兵”。论兵,儒者末事,言喜无害。喜,非嬉戏之戏,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 回也好学,岂是薄颜回乎?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苟恣所见,岂足听哉?
修见韩退之舆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尹师鲁,忠义耿介之贤豪,文章才华之秀士,在北宋朝廷政治斗争的激流漩涡中,在文学运动的潮头浪谷间,走完了他坎坷颠沛,却也际会风云的人生历程,病故于贬所。年仅46岁,他临终没有卧在病榻上,而是伏在几案上离去的。
尹师鲁,名洙 (1001—1047),河南 (今河南洛阳) 人。他是著名的散文家,文学上的革新者。宦海沉浮,文章际会,使欧阳修和尹师鲁成为政治、文学上的知交。对他的死,欧阳修怀有深切的惋惜与同情,在他死后的第二年 (庆历八年) 写下了情词剀切的祭尹师鲁文和尹师鲁墓志铭。
“墓志铭”做为一种文体,就其内容与形式而言,与墓碑 (或曰墓表)并无多大区别,只是二者的作用不同。志者,记也,兼有标志之意; 铭者,名也,兼有镂刻之意。是恐怕年代久远,墓地表面变迁,而使墓主人的名姓、生平被岁月淹灭失传而设的,埋于墓前三尺许的地下,所以叫“墓铭”。而墓碑则是立在墓前地面上,供后人祭吊而设的。
墓志铭一般分志和铭两部分,志是散文,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生年,寿考、卒葬日期及子孙世系。铭多用韵文,咏叹死者,寄托哀思。也有在志铭前记写作缘起的,叫“墓志铭并序”。
庆历五年秋七月尹师鲁被贬。七年四月十日病卒于南阳,靠朋友出资帮助,妻子于庆历八年将灵柩归葬河南。欧阳修作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完成后,遭到很多人的非议。遂宁府有石刻记载。尹师鲁的妻子张氏对志文的简略很是不满。新科进士孔嗣宗到颍州留居半月之久,找欧阳修辩论,指斥墓志铭的不是。欧阳修写了论尹师鲁墓志铭以释其意。据此石刻说,欧阳修曾将志文有所添换。但看墓志铭本身,浑然一体,了然无痕,全无添换迹象。这其间欧给孔嗣宗的书信却说:“……此不当辩,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故其妻子不是,故须委曲,近曾录寄范公,今录奉呈,为语尹氏。”从“故须委曲”四字看,他是对指斥做了某种妥协的。但在与杜䜣论祁公墓志书中又说:“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为墓表云云,然则当时固无甚添换也。”论尹师鲁墓志铭 中有“……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由此观之,或许他“录寄范公,今录奉呈,为语尹氏”的,就是这篇论辩文,这就是对尹妻张氏的“委曲”并有所“添换”了。文中又有“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似叙确有添换。这就是欧阳修碑志文章中“范(仲淹)碑”、“尹志”两重公案中之一案。
论尹师鲁墓志铭不仅一一解释了孔嗣宗的质问,同时,也就“尹志”的写作意图与特色提出了撰写墓志铭的一系列理论原则问题。欧阳修首先回答了关于志文过于简略的指责,并提出了墓志铭创作“文学简约”的原则。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比起尹师鲁之子请太尉韩琦(字雅圭)写的“墓表”,确是简略得多。但欧阳修在论文中指出,不能“但责言之多少”而“不考言之重轻”。
作者先总论一句“天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才能”。既然天下人皆知,自然简略无妨。然而,简约绝非对死者的轻慢。他写师鲁的“文学之长”仅用“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如此看来,他论“师鲁之文不薄矣”。“推其文学”仅用了“通知古今”,而“此语必求其所当者,惟孔、孟也”。他评师鲁之文学亦可谓不低了。述其议论,但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这个断语也着实不轻了。说到师鲁的才能,只大略写了“师鲁历贬”、“深知西事”、“师鲁得罪”的经因与政绩,虽然简略,却“使天下人尽知师鲁材能”。
为了使志文简约,论文中还提到“互见法”。文中没有写“近年古文自师鲁始”,是因为“范公祭文已言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并举皇甫湜韩文公墓志和李翱为韩愈写的行状之不同为“互见”之显例。在志文中作者直接运用这一原则,没有写死者的家世,原因是“尝铭其父之墓矣,故不复次其世家焉”。
文章简约,选材必须精当。这是欧阳修提出撰写墓志铭的又一原则。他说“其事不可偏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在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中也强调“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他解释说“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虽只两件事,几句话,却完全表达了对师鲁高尚品格的赞誉之情,“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的确,精当的选材果然成为传神之笔。
在论证并非“作古文自师鲁始”时,作者提出了态度严肃,论断准确的原则。这不仅表现在为“取信”而“举其需者”的认真选材上,也表现在对尹师鲁的评价上。他不认为“古文自师鲁始”,因为在师鲁之前有穆修,郑条等人以及“大宋先达甚多”。他坚持“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才是实事求是的。给孔嗣宗的信中,辩之更详:“东方学生皆自石守道(石介)诱倡,此人专以教学为已任,于诸生有大功,与师鲁同时人也,亦负谤而死,若言师鲁倡道,则当举天下言之,不遂见掩,于义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则不可,故此事难言之也。察之。”欧阳修坚持实事求是,取信于天下,终不因死者亲友的质问,也不因是死者的至交而徇情,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反对了唐宋以来的“谀墓”之风,这种“不虚美、不溢恶”的创作态度,使唐代大家韩愈也为之相形见绌。
面对“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的指责,作者提出“春秋之义”与“诗人之义”的原则,亦即“文简而意深”的原则。他说“痛之益至,则其词益深”“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所以他认为前面写了“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师鲁“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而这冷峻沉郁的叙述,却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十二字铭文不能再短了,并没有“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然而却深沉含蓄,其言有尽而其意无穷,婉惜与愤懑之情如冰冷沉重的铭文刻石,轰然压上读者心头。
这是一篇说理的议论文,论述周到精当已属难得,更难得的是论文也如墓志铭原文一样从头至尾充满感情色彩,浓烈的思念情绪充盈始终。随看他对文章简约的论述,对师鲁的赞颂也步步推向高潮。在论述其文学、其议论、其才能之后,笔锋一转:“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如此高才算不了什么,师鲁的“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才是其至高的美德。这便把对尹师鲁赞扬推到了极至。紧接着,他论述墓志铭写师鲁的“以贬死”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笔调如临万仞高崖落无底深渊,大起大落,更加重了“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的悲剧气氛,似乎使我们感到作者胸中汹涌翻腾的热血的波涛。
文章最后更是笔笔动情,也把说理推到极端。他说韩愈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为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所以他为尹师鲁写的志“盖为师鲁义简而意深“——他所以写这样简约的墓志铭,完全是遵循师鲁之志的。他坚信他的作品好友师鲁是完全理解的,“唯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死者有知,必爱此文”。真是两心相印,知交的情怀,油然而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原则,以及对朋友的忠诚,文章以“所以为吾友尔,岂恤小子辈哉!”作结。感慨系之,言尽而意远,似又把读者带上尹师鲁艰辛的仕途,带到了贬谪的路上,带到了病危的几前……
论文的又一特点,是由其特定的读者对象决定的。对方并非政敌,而是作者的朋友,对死者有着同样深切的痛悼思念之情,这就决定了文章不能慷慨陈词,激扬文字,而是款款道来,娓娓动听,使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论辩是诚恳的。开头便心平气和,“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论议才能……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完全是劝诱商量的语气。当回答“师鲁‘喜论兵’”的质问时,他不正面反驳,而说“言喜无害”“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又用问话的形式开导对方,难道“孔子言:回也好学”就是“薄颜回乎?”他的行文运用了类似“顶针”的修辞手法,“述其义”,“既述其义,则又述其学”、“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才能”……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使文章结构细密严谨,说理透彻,如剥茧抽丝一般。想来,经过半月的交谈,孔嗣宗应该是心悦诚服地离开颍州的。
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铭是一篇难得的有关碑志文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墓志铭的创作原则,对宋以后的墓志铭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集文学家、历史家于一身,综合两个方面的要求,把史笔与文心结合起来,开创了后古文家“义法论”的先河。他以后的王安石、明朝的黄宗羲等人都对墓志铭的创作原则有所论述,很大程度上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尹师鲁如九泉有知,大概会向欧阳修含笑而揖,赞赏他的古道热肠,感谢他对其未竟文学事业的执著努力。
-
萧散弓惊雁,分飞剑化龙。悠悠天地内,不死会相逢。
-
《望岳》 年代:唐作者: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校 作品赏析 【注释】:
-
在甘肃境内的渭河流域循丝绸古道分布有许多石窟,有天水麦积山、仙人崖,甘谷大象山、华盖寺,武山的木梯寺、水帘洞、禅殿寺石窟,西和的法镜寺石窟和八峰崖石窟等,其中以麦积山石窟规模最为宏大。 (1) 武山石
-
春始,以学士人学宫而学之,始入学必释菜,礼先师也。|什么意思|大意|注释|出处|译文
《春始,以学士人学宫而学之,始入学必释菜,礼先师也。》什么意思,句子大意,出处,译文,注释,点评。
-
我是扬州人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
-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天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苦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
-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
-
本文主要为您介绍有关走向复兴的古诗词,内容包括复兴中华的诗句,关于走向复兴的诗歌在晚上10点前给我,复兴中华的诗句。诗中之侠(复兴中华)诗词选集(五绝部分) 五绝·听网友语而感 岁晚寒将至,谁言暮野空。有千棵硬草,我亦在其中 五绝·雨弦(今声) 树上黄
-
足下复不第,家贫寻故人。且倾湘南酒,羞对关西尘。山店橘花发,江城枫叶新。若从巫峡过,应见楚王神。
-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