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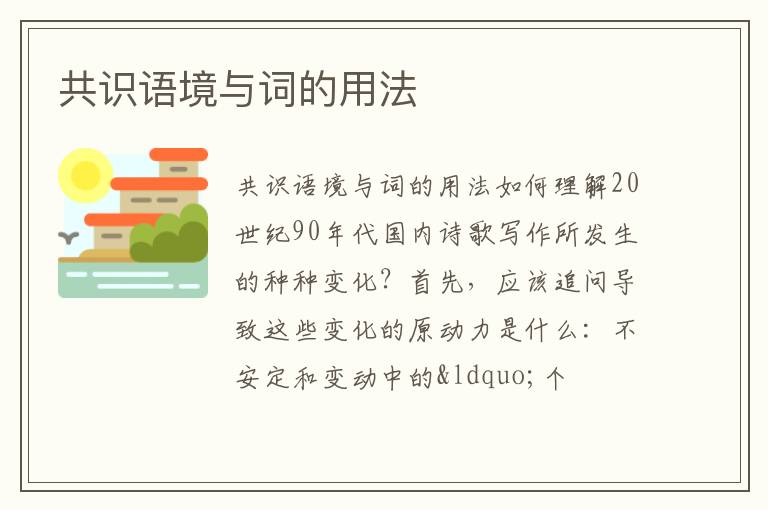
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
如何理解20世纪90年代国内诗歌写作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首先,应该追问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动力是什么:不安定和变动中的“个人信仰”(诗人对形式和精神的关注强化到一定程度就是信仰),还是寓于更大的变动和不安定中的“集体无意识”力量?其次,应该追问这些变化对诗人意味着什么——例如,现实中的自我与精神自传的自我在某些诗人的近期作品中越来越微妙地混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具有重合性质的自我形象既非现代主义的“自我中心”(自恋或自渎)的产物,亦非后现代主义的“分裂分析”的产物,它甚至不是修辞策略的产物。诗人们并不想为这一重合的自我发明一个本质,然后从它出发去重新命名现象世界。我以为,如上所说的自我的重合,实际上意味着某些较为敏锐的诗人将词的问题与物质世界的问题、风格的历史与真实历史合并在一起加以考虑,这一合并指向创意和写作相互交织的、要求得到澄清但最终并不透明的和个人化的诗学境界,因此重合过程加以强调的不是个别印象,而是印象之间复杂的变化的联系。换句话说,关联域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诗人和批评家们广泛地谈论。我在这里所说的关联域问题,不仅涉及词与物、个人与世界、风格与历史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它以一种极为隐秘的方式涉及了词的内部关联问题:显然,如何理解一个词与如何使用一个词,两者是有差异的。我正是在这种差异的提醒下提出了“反词”命题,它所关注的是同一个词作为圣词和作为寻常词语,对我们的写作和阅读有着怎样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对如何使用一个词的强调甚至对如何理解一个词的强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特征。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词的意义是由如何使用这个词决定的。我的理解是,词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为每个词都有多种用法,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将用法问题提到如此之高的位置上予以强调,存在着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所以我要特别指出个人写作的语境问题:词的任何个别用法必须接受共识语境的过滤。我所说的共识语境,一是指表明我们共同处境的历史语境,二是指从历史语境分离出来的诗学语境。了解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关键是了解个人话语是如何被导入上述两种语境的对质之中的。
作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诗歌”的倡导者之一,我坚持认为当代诗歌是一门关于词的状况和心灵状况的特殊知识。使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在产生过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和诗学理论家海子、西川、臧棣、骆一禾的北京大学,诗歌也不得不置身于来自初级常识的种种诘难之中。在这篇匆匆写出的短文结束之前,我要说:当代诗歌肯定是对初级常识的一种冒犯。一年前去世的诗人布罗茨基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分析了捷克文人总统哈威尔后共产主义噩梦一文中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方便。我要加上一句:当代诗是不方便的。这种不方便恰如英国诗人威廉·布洛克在耶路撒冷一诗中所写的:没有轮子的轮子发明出来,为了让年轻人外出时感到困惑。
1990年4月7日于成都
-
美哉水,洋洋乎,我怀先生,送之子于城隅。洋洋乎,美哉水,我送之子,至於新渡。念彼嵩雒,眷焉西顾,之子于迈,至於白马。白马旧邦,其构维新,邦人流涕,画舫之孙。相其口髯,尚克似之,先生遗民,之子往字。
-
郡后主婿宫郡后主婿宫 【原文】 本朝宗室袒免[1]亲女出嫁,如婿系白身人[2],得文解者为将仕郎,否则承节、承信郎,妻虽死,夫为官如
-
书香意趣前几天办完事之后,闲逛到书店。琳琅满目的图书放在书架上,古色古香,图文并茂,鲜艳的封面,让人目不暇接。每次逛书店都感觉大脑
-
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莫辨荆吴地,唯余水共天。渺弥江树没,合沓海湖连。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
-
沈周 看云疑是青山动,谁道云忙山自闲。 我看云山亦忘我,闲来洗砚写云山。 侵晓溪山半是云,草堂亦许白云分。 故人到此云相接,欲去还须云送君。 【评说】 本诗选自汪砢玉《珊瑚网》卷三八、卞永誉《式古堂书
-
佯为不闻【原典】吕蒙正①拜参政,将入朝堂②,有朝士于帘下指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为不闻。既而③同列必欲诘其姓名,蒙正坚不许
-
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还将旧曲,重赓新韵,须信吾侪天放。人生何处不儿嬉,看乞巧、朱楼彩舫。
-
书法是我国一门有很悠久历史的艺术,而美学严格说来却是西方近代产生的一门学问,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美学”这门学科一般都认为是近代十八世纪德国一位叫鲍姆加登的哲学家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
-
【原题】:夜宿昭亭寺舍弟以公事书城中与梅公泽邵公序昆仲待月山亭取酒共饮明日舍弟有诗次其韵
-
渊明避俗未闻道,此是东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闻道更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