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之《儒林外史·鲍文卿》内容解读与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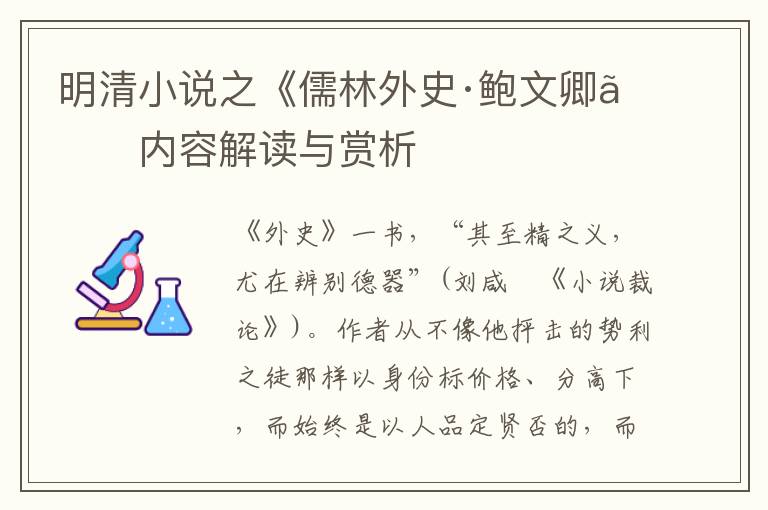
外史一书,“其至精之义,尤在辨别德器”(刘咸炘小说裁论)。作者从不像他抨击的势利之徒那样以身份标价格、分高下,而始终是以人品定贤否的,而且由于他对上流社会失望,又特别注重用贱行中的君子风来侧击、反讽那些“君子”队伍中的贱行,于是有了身为戏子,而品德却是上上人物的鲍文卿。
常言道:大块一戏场,古今一戏局。身为戏子的鲍文卿该如鱼得水、当行擅场了,可他偏偏是个呆子! 他当年的同行、演老生的钱麻子经二十年移风易俗,如今那衣饰、气派俨然翰林、科、道老爷,而且钱麻子自称,眼角里根本不看那些“学里酸子”。志在“凿破浑沌”的张文虎于此处评点道:“今世读书人无异书生戏子” (天一评),看来至少从吴敬梓到张文虎时期读书人如戏子者正复不少。人们都在如戏场之大块中追求着易位效果,充分表演,以期“各得其所”。鲍文卿即为戏局一角色,自然也得登台演出,但他不是用流行道具,而是用真诚来进入角色,并无怨无悔地演到自己谢幕时。没有那追求易位体验的浪漫、热情,在人都不安其位时,他偏偏守份到底,从一而终,其迂腐简直是不可救药,太“傻冒”了。
他最符合作者心意之处也正在这里,作者偏偏要树立这一形象以呼唤“傻子精神”。“傻子精神”是任何靠道德治天下,重信仰和观念而轻利欲的学派或个人都提倡、推重的。吴敬梓在公心讽世的同时,志在筑构一条道德长堤,以阻遏那弥漫于全社会的“五河县式”的势利风习,骂贪扬廉、斥邪树正、击妄拥诚,原为一体两面,作者也是双管齐下的。这诚、正、廉与那贪、邪、妄相比,便是市侩眼中的呆子标本了。外史中,鲍文卿、虞育德都是呆功称绝的典范。
鲍文卿最大的呆气是不贪,这也是他的立身之本。碰着嘴唇的不吃,到手边的不拿,坚守着“须是骨头里挣得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这样一个极朴素又高级也艰难的信念。那两个口口声声叫“鲍太爷”,极尽奉承之能事的书办恳求他在向鼎面前说个情,只要答应去说就“先兑五百两银子”,却热脸贴在凉屁股上,被鲍文卿一番“公门里好修行”的宏论说的“毛骨悚然、一场没趣。”其实何尝不让所有“公门里损阴”的人毛骨悚然?只是有些人早已刀枪不入了。崔按察司让他去向鼎处领取按惯例存放的“正当”的款项,本该是授受两欢喜的事,鲍文卿却坚拒不收,而且那理由也蛮新鲜,硬说那银子是朝廷给老爷的俸银,而自己是贱人,用了朝廷的银子非折杀不可。若是严贡生在旁,肯定会急出眼珠子来,换上权勿用则自有一番“你的就是我的”的高论。向鼎起初对鲍文卿是完全把他当成上司的人,又有恩于己,他给鲍文卿五百两银子只是为了了帐,那时还谈不上“平等”的友情。是鲍文卿的呆气感动了向鼎,遂有了以后一段情缘。鲍文卿公心之呆气,反而变成了情感、利益投资,这对鲍文卿来说是额外收获,他是施恩不望报的,何况,对知县老爷、朝廷命官,他连“施”这个概念也没有,他为向鼎在按察司面前说情,也只是敬重斯文、怜惜名士之意。
无欲则洁,不贪则诚,洁诚至,则其人正矣。所以,鲍文卿虽为向鼎之“帮闲”,却无篾片之惯态与劣迹。他对向鼎是自幼仰慕、亲炙为乐,绝不是为了揩油。外史中那些可耻、可笑的人物,总因有一欲念,或贪财慕利、或干求名位,现出种种丑态,而鲍文卿“安贫守分”,毫无邪欲,不求份外“洋财”,更无其他虚荣心,于是,在作者和向鼎眼里,便成了“傻子精神”的表率,用他们的原话来说就是君子之风。
如果说鲍文卿对向鼎的态度还暗中有个“朝廷的规矩”在为纲支目,那他对倪霜峰老人的态度,诚如“天一评”所云:“文卿不可及。” 陌路相逢,真心相待,商量修补乐器的过程,事虽极琐碎,却很动人。鲍文卿绝无居高临下的雇佣观念,更无刻薄心理,是“仁者爱人”古训的最佳例释。酒楼上二人的晤谈,即可视为“读死书”之斯文人的祭文,又是鲍文卿慈心热肠的别传。他对倪老爹是真正的仁至义尽,料理完倪老爹的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一如向鼎哭“老友文卿”! 真有人类皆弟兄之博爱情味。鲍文卿对上不谄、对下不欺,待人至诚,性情醇厚,堪称君子,当得起“义民”。
向鼎给老友文卿题写铭旌时,只是展示着向鼎不俗的情怀,并未说明鲍文卿什么。而当季守备以与梨园同席为非、脸上不觉有些怪物相时,向鼎讲的那一番话却是真可以当作鲍文卿的“墓志铭”的:“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 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鲍文卿刚返南京看见钱麻子那样的屁精戏子与儒生衣着、座次等外观上的倒错时,他好不受用,以为戏子“越位”犯规,其实他的君子之行与那些中了进士的构成另一种颠倒关系:“名儒而实戏也” “名戏而实儒也”(卧评)。“义民”鲍文卿也佐证了杜少卿的判断:那学里的秀才未必好于奴才! 把教养里的词藻当了真的,不是那些腐儒、陋儒、小人儒,以及一些名儒,而是鲍文卿这样的戏子。这极为深邃的讽刺,不是笔墨书写出来的,而是由那个充满“倒挂”、“错位”的世界本身的荒谬性构成的。
鲍文卿的“君子之行”、“平生的好处”,简而言之,即“安位守分”、“仁者爱人”。他以古道热肠待人的仁厚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他那洁正不贪的做人原则也是针砭那无耻之徒的药石。但这个形象绝对没有作者期待的那种醒世之晨钟的作用。道德治天下,关键在于自律,那个“无智、无聊、无耻”的“三无世界”的活宝们已无自律之本基,就是神州大地处处都有鲍文卿又有何补益! 全社会的颓风已无情宣告:儒家道德治天下的传统是失效了。可是作者还在鼓吹守分思想,并向往用古礼古乐为“末世之一救”,这就显然是一种真正的呆气了。人们学习“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鲍文卿不是既便宜了丑类,又方便了昏庸的“牧人”么?作者肯定、表彰鲍文卿恭谨地遵守礼法,从不越奴隶之位的意图,再清楚不过地披露着他那世家公子的遗风,对“朝廷体统”的维护。在全书中,作者一直把“守分”与否,作为划分“贱行”中君子与小人的一条标准。这些都证明着作者尽管已经有了进步的世界观,但还是束身于名教之内。鲍文卿对朝廷体统,吴敬梓对守分观念,都犯的是杜少卿那个“毛病”: “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我们几乎可以说:鲍文卿是外史的一个“全息现象”——从中可以同时看出外史为人性立法的优点与缺失。他知人之哲,拒利之洁,是不亚于“名儒”的,而太“卑以自牧” 则真是迂守“戏局”规矩的呆子了。
-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① 。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
-
魏王大瓠实五石,种成濩落将安适。可怜公子持十牛,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负不羁才,従车数到单于台。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将军何人哉。夜逢怪石曾饮羽,戏中戟枝何足数。誓将马革裹尸还,肯学班超苦儿女。封侯卫霍
-
原文: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译文夜半醒来听到了浓重的露珠滴落声,打开门来面对愚溪西边依稀的菜园。一轮清冷的月亮正在东边的岭上升
-
同日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进行墨城湖阻击战 : 5月28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一部,在墨城湖一带阻击从诸暨倾巢出犯的伪军独立第4旅。激战5个小时;将该部击溃。伪独立4旅3个营长、7个连长被当场打死。是役
-
今日西京掾,多除内省郎。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清秋便寓直,列宿顿辉光。未暇申宴慰,含情空激扬。司存何所比,膳部默凄伤。贫贱人事略,经过霖潦妨。礼同诸父长,恩岂布衣忘。天路牵骐
-
【注释】 选自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亨:通“烹”。 藏:收藏。 【赏析】 韩信是西汉第一大功臣,他离开项羽,效力刘邦后,从定策汉中,俘虏魏王,生擒夏说,诛杀成安君,破赵胁燕,到东平国,南灭
-
宋·苏轼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
受之未尝形色【原典】韩魏公因谕①君子小人之际②,皆应以诚待之。但③知其小人,则浅与之接耳。凡人之于小人欺己处,觉必露其明以破之,公
-
龟之气兮不能云雨,龟之木卉兮不中梁柱,龟之大兮只以奄鲁。知将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归辅。
-
清·朱彝尊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这是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