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贾谊论》原文|赏析|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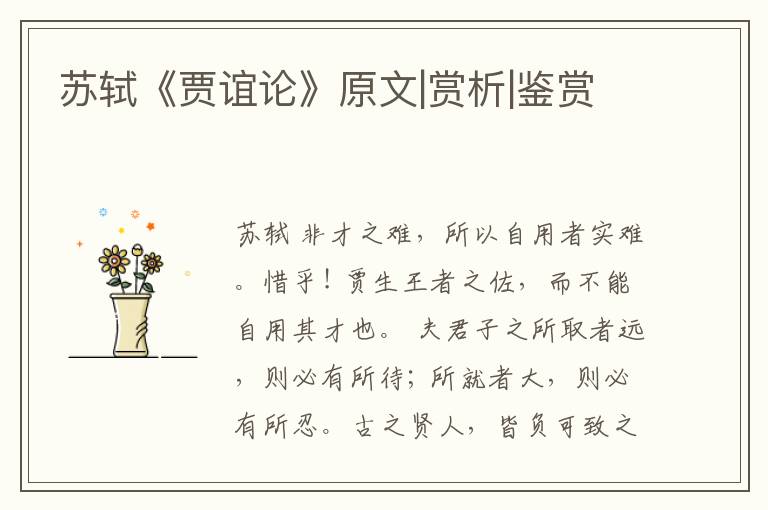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 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 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之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如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宋人好议论,好辩论。不但与古人辩,还要和今人辩。他们喜欢标新立异,充满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喜欢怀疑,喜欢作翻案文章。如果说汉学的精神是“我注六经”,那么宋学的精神便是“六经注我”,正好与汉学相反,这种精神在文学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宋学的代表。他们都是文学家,也都是政治家。王安石在政治上成就更大一些。苏轼在政治上保守,文学上成就更大一些。但他们都是体现着宋学的精神。苏轼的贾谊论就是一篇与陈说唱反调的文章。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18岁的时候便以诗文著称于世。文帝对贾谊的才能与建议颇为赏识,一年之中,就提拔他为太中大夫。后来,文帝又准备任贾谊为公卿,但是,因为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重臣阻挠和反对,不得已而作罢。不久,出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以后文帝又想起贾谊,曾在宣室召见他,咨以鬼神之事。贾谊随即拜为梁怀王太傅。文帝前元十一年 (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当时贾谊才33岁。
贾谊具有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在汉初太平景象的背后看到了潜伏着的社会危机。贾谊的政论文笔锋犀利、铺张扬厉,气势充沛,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议论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而不浮切、充满济世救时的热情。贾谊的才华历来为人所赏识。他那不幸的命运,赢得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子的同情。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著名的绝句贾生,讽刺了文帝的求贤、敬贤、表达了他与贾谊千载之下的心心相通: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苏轼对贾谊的才华也十分欣赏,对贾谊过早的逝世表示十分惋惜,他俩的政论文的风格也不无相似之处,都是畅达无忌、议论风生的纵横家的风格,可是,苏轼的这篇贾谊论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贾谊的遭遇,从而得出了新的结论。全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作者开门见山,提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这样一个中心论点。这个论点与传统谈人才的文章是大相异趣的。历来都是讲人才难得,讲识别人才、尊重人才,如韩愈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可是,苏轼却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这个论点落实到贾谊,便得出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结论。一下子扣紧了题目。接着,作者就此进行了简要的论证,指出君子目标远大,要能忍耐,等待机会。古代的才能之士,他们之所以未能得以舒展抱负,“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这样,文章又暗中回到了“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的中心论点,并隐隐地指向了贾谊。
第二个层次,引圣人孔孟为例,用反证法来证明人才之不能尽其所用,“未必皆其时君之罪”。这一个层次又可以分为三个小层次。作者没有明确提出他要反驳的对象,但是,实际上他的文章是以“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皆其时君之罪”为靶子的,所以全文充满论辩色彩。第一个层次已经通过正面的论述把所要反驳的观点摆了出来。在第二个层次,便进行有力的反驳。作者首先退一步说“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接着就顺着对方的思路论下去,得出一个显然是荒谬的结论:“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结论的荒谬自然证明了对方思路的错误。紧接着,作者就以孔孟为例,说明有才之士,要有藏身待时的韧性。孔子、孟子,生前都未曾得志。生当诸侯吞并、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孟却来大讲仁义,没人听他们的。可是,孔孟都是积极人世,“知其不可而为之”,所谓“尽人事,听天命”。“荀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孔孟遭到的挫折比贾谊大得多。他们赶上的是乱世,“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尚且这样不灰心,不泄气,相比之下,贾谊的胸襟识度就大大不如了。汉文帝是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后人的运气还赶不上贾谊呢。所以,这第三个小层次的结尾就自然地得出了“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的结论。这一结论与中心论点相呼应,以历史人物,以圣人为例,论证了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观点。
第三个层次,从贾谊的具体处境出发,设想贾谊可行的策略,以此证实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论点。作者先分析了周勃、灌婴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周、灌都是跟随汉高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又是铲除诸吕,迎立文帝、安定刘氏天下的功臣。他们所进的谗言,足以动摇文帝对贾谊的信任。贾谊少年新进,立足未稳,求治心切,进言太急,自然招来这些老臣宿将的忌恨。接着,作者又为贾谊设想了切实可行的策略,要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然而,事实上贾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受挫折,便“萦纡郁于闷”、“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于是,作者得出贾谊“是亦不善处穷者也”的结论,而“不善处穷”亦即不能自用其才的主要表现。所以,苏轼所谓的“自用其才”,还是儒家传统的观念:得志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
第四个层次,对前面的论证加以补充,使之更为全面。作者既已指出才能之士要善于处穷,要学会忍耐,不要一遇挫折便颓废伤怀,又肯定了高世之才确实难得一展雄图的历史事实。既指出了贾谊“不能用汉文”的一面,又表示了对贾谊的同情。说明要做到人尽其才,需要君臣双方的努力。
这篇不足千字的历史人物论,见解新颖,道前人所未道。有理有据、思路清晰。有反证,有驳论,也有正面的论述。虽是翻案文章,却立论稳妥,无偏激之病。
-
【经文】 凡奉者当心 ① ,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 ② ;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 ③ ;士,则提之。凡执主器 ④ ,执轻如不克 ⑤ 。执主器,操币圭璧 ⑥ ,则尚左手 ⑦ 。行不举足,车轮曳
-
南北东西无所羁,挂冠目在胜分司。探花尝酒多先到,拜表行香尽不知。炮笋烹鱼饱餐后,拥袍枕臂醉眠时。报君一语君应笑,兼亦无心羡保釐。
-
寿陵 ① 余子之学行于邯郸 ② 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 直匍匐而归耳。 ——《庄子·秋水》 【注释】 ①寿陵:燕国地名。②邯郸: 赵国国都,故址在今河北邯郸市,城周达数十里。 【意译】 有个寿陵少
-
【析】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这是一篇表现深切,格式特别的白话创作小说,它的出现,标志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 小说由十三则日记组成,首则点出我的怕
-
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仰看云天真蒻笠,旋收江海入蓑衣。
-
俞安期《漓江舟行》明山水诗鉴赏 俞安期 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 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山水小诗,表现了诗人面对广西漓江风光时超逸洒脱、喜不自胜的心境。 漓江两岸
-
本文主要为您介绍完成工作打算古诗词,内容包括阐述下一步工作计划的古诗词,努力工作,实现目标的诗句,工作励志古诗词。原发布者:cdsabestc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随
-
泛指那些侧重于直接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感受,注意于主观抒写的不讲究骈偶押韵的文体。按传统说法,散文是与韵文、骈文相区别的散体文章。广义地说,除了诗、词、曲、赋以外,一切无韵无律的文章,诸如人物传记、回忆录
-
此诗以十分形象化的手法,抒发自己的丹心热血。 首句“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此诗虽为登临之作,却不像一般登临诗那样开篇就写景,而是总括作者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卓绝战斗生活。“寒”,既指苍茫清寒的海色,同时也暗示旷日持久的
-
《烛之武退秦师》 此文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作者相传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题目为后人所加。清林云铭《古文析义》说:“烛之武为国起见,说秦之词,句句悚动,有回天之力。其中无限层折,犹短兵接战,转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