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言·可杀而不可使为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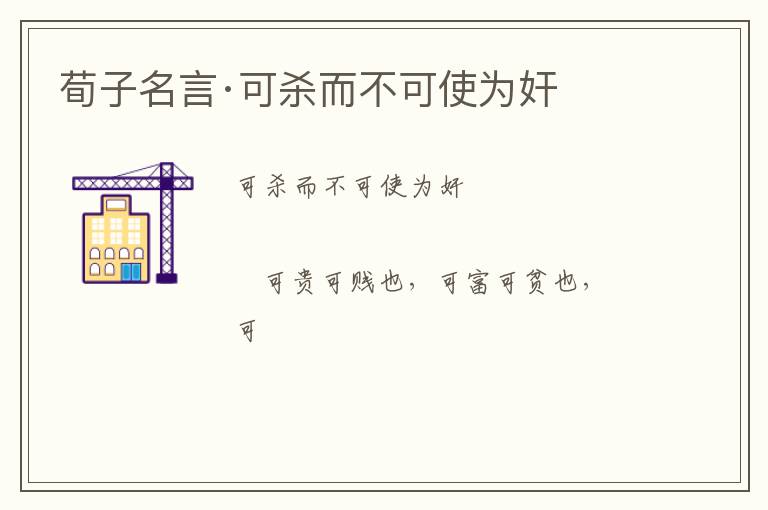
可杀而不可使为奸
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仲尼)
【鉴赏】 君主制,实在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尴尬。人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的。社会群体必须要有结构秩序。时代越靠前,社会对这种结构秩序的需求就越迫切。这样,总领其事的权威君主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具体到中国,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又天然要求这种权威君主以世袭制的方式长期存在。于是,“事君”作为一种义务,就在社群内部长期固定下来了。
不同于欧洲骑士之侍奉领主,日本武士之忠于将军,中国的士大夫除了“事君”之外,还有另一种“事”,那就是“事天”。
中国一向缺乏成型的宗教,但没宗教不代表没信仰。从上古开始,在中国士大夫心中,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天”的意识。“天”高于“天子”,这应该是中国士大夫共同的信念。所谓“事君”,实是要以“事君”的外在形式,来行使“事天”的实质内容。
但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形式与内容往往要产生冲突。如果每个“天子”都能够做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大明),那大家自然可以心甘情愿地“媚于天子”(诗经·大雅·卷阿)。可如果“天子”逆“天”而行呢?我是遵从“天子”,还是越过“天子”直接去“替天行道”? 面对这样的抉择,人往往是要精神分裂的。
到得后来,随着君主集权制的逐步确立,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宗教感也越来越淡薄,所谓“事君”和“事天”,也就渐渐地不再有什么区别了。“事君以事天”变成了“事君即事天”。古老的“事天”,不再具有形上感,而成了一种微妙的用心艺术。对于这样一种艺术,描述得比较细致的是荀子,他说:
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仲尼)
这好像是在向人传授“事君指南”。其实不然。这是在说“事君”,但也是在说“事天”。只是这种“事天”与“事君”高度重合,只有在其道德底线“可杀而不可使为奸”那里,才依稀透出一点古老的“事天”本色。
儒家的“天人合一”,到此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真正的“事天”,必须摆脱“事君”的枷锁,如庄子那样,挥斥八极,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在过去,只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修行人能够做到,而在封建君主制业已废除的今天,则应该可以普遍地实现了。
-
这一首,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揉合,融为一体:首句写名花与倾国相融;二句写君王的欢愉,“带笑看”三字,贯穿了三者,把牡丹、贵妃、明皇三位一体化了。三、四句写君王在沉香亭依偎贵妃赏花,所有胸中忧恨全然消释。人倚阑干、花在栏外
-
[明]于谦寄语天涯客,清寒底用愁?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于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
-
【名句】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注释与译文]最直的好象是弯的,最灵巧的好象是笨拙的,最善辩的好象是不善言辞的。这段话,含有朴素的辩证法。 参考文献 《老子》
-
【宋】苏轼 游靳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注释】 蕲水:旧县名,治所在今湖北浠水。清泉寺在城
-
宋·苏轼2顷岁3,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4,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
-
风流走了水里的影子,水打落了风中的叶子。时间来得太安静,去时也没有声音。只剩下表针走动时寂寞的嗒嗒声。沉在水底的记忆慢慢洇开,青蛙
-
我有方外客,颜如琼之英。十年尘土窟,一寸冰雪清。朅来従我游,坦率见真情。顾我无足恋,恋此山水清。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昨日放鱼回,衣襟满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载乌程。山头见月出,江路闻鼍鸣。莫作孺子
-
孟子 孟子曰: 舜发于畎亩之中 (1)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2) ,胶鬲举于鱼盐之中 (3) ,管夷吾举于士 (4) ,孙叔敖举于海 (5) ,百里奚举于市 (6) 。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7)
-
俞安期《刘仙巖十咏爲张质卿赋(并序):中天楼》写景抒情诗词赏析
刘仙巖十咏爲张质卿赋(并序):中天楼刘仙巖(1),仙人刘仲远所居。抵山之半,入户旋返而上登者,爲升真洞,仲远鍊真沖举(2),咸在兹焉。左
-
茅盾《雷雨前》原文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之间在形式结构上有一种巧妙的对应关系,外在世界的力影响主体内在世界的力,能激起人的相应的情感反应,这就为文艺作品的象征作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茅盾
